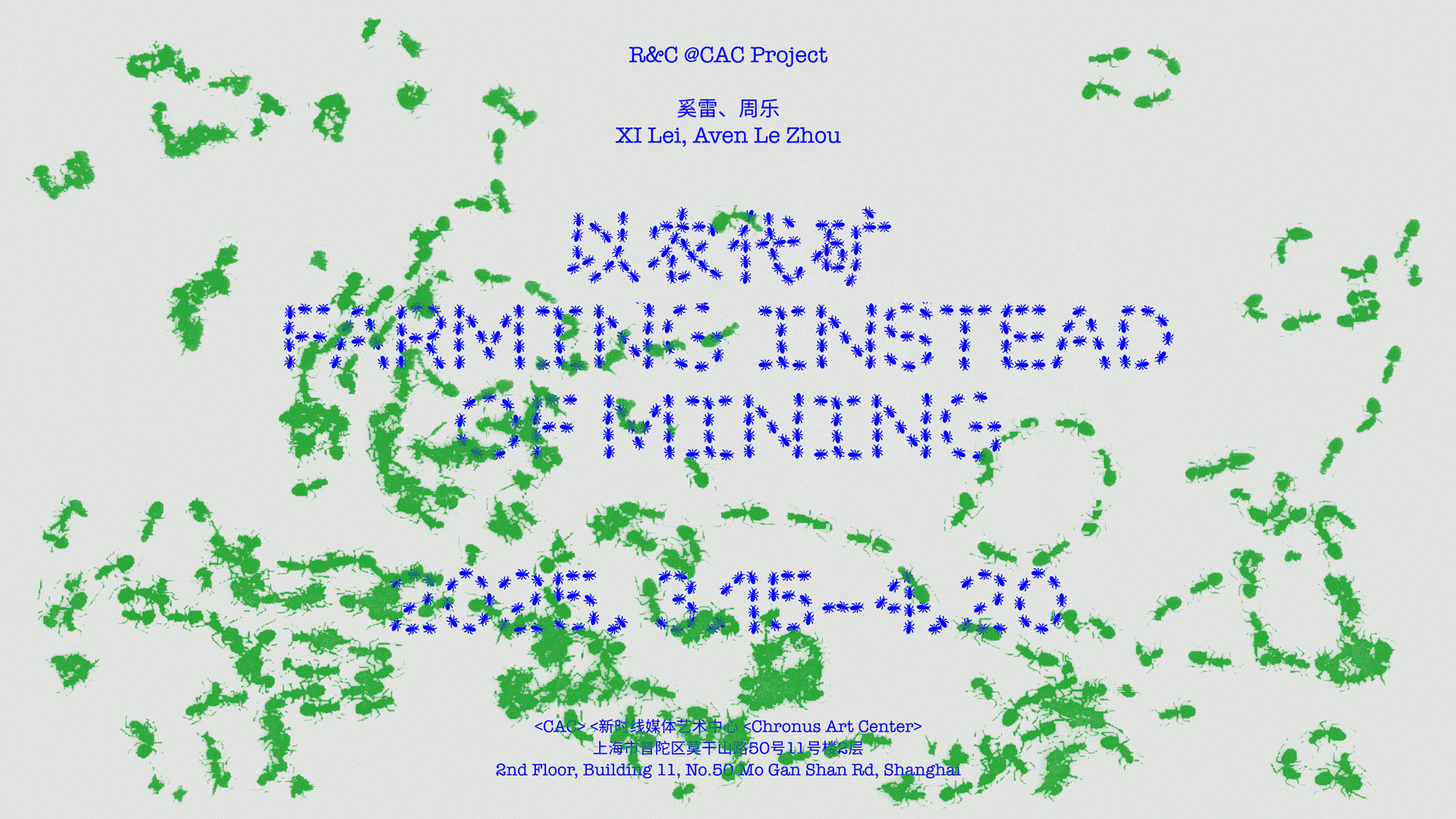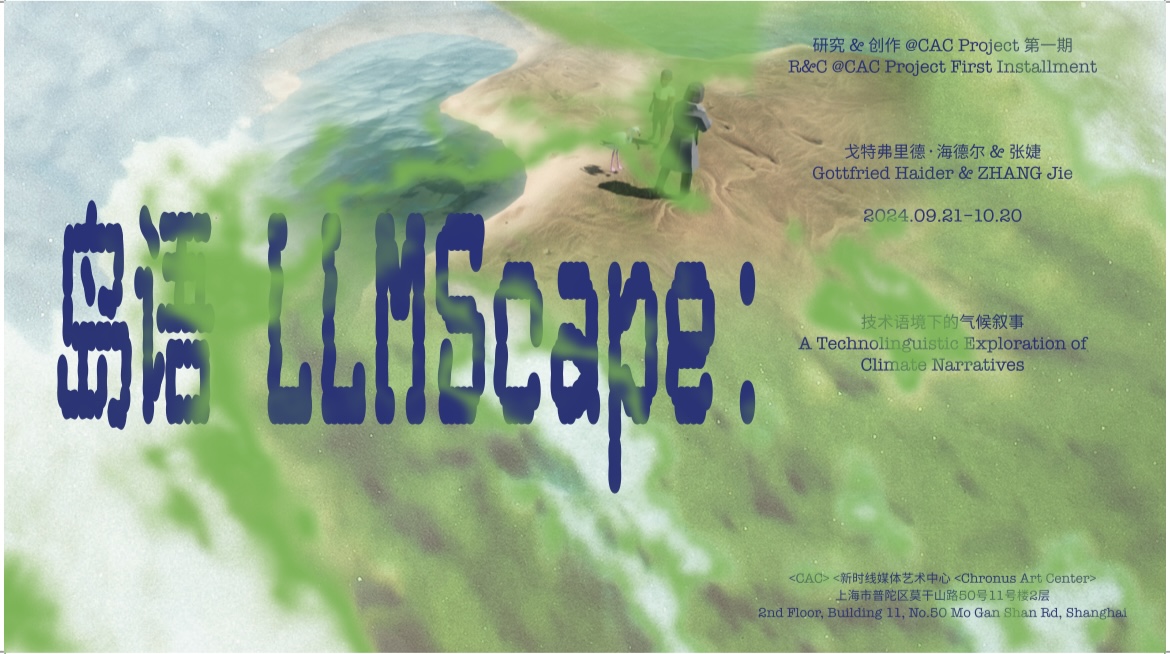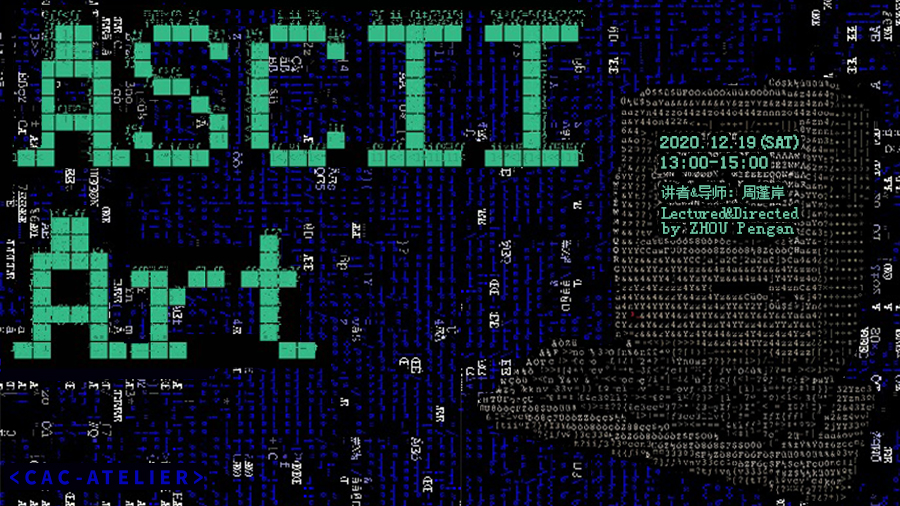嘉宾:Raqs媒体小组与祖雷卡·乔达里
时间:2013-08-24 15:00 ~ 2013-08-24 16:00
地点:莫干山路50号 M50艺术园区18号楼
“而后,我们的眼睛开始工作,游历。”
《塞康德拉巴德之所见》是Raqs媒体小组和同样在印度德里工作的剧场导演祖雷卡·乔达里合作的作品。这一由卡维亚·穆尔蒂和巴格瓦蒂·普拉萨德表演的50分钟戏剧,在费利斯·比特于1858年摄于印度勒克瑙的一张照片的投影前展开。演出的情节由Raqs和乔达里共同设计,而Raqs又用文本和录像对演出进行干预。费利斯·比特是一位先锋性的旅行摄影家,他用照片记录了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印度大起义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演出中使用的这幅照片呈现的是在宏伟的废墟前的一个临时灵堂(这是1857年东印度公司的部队在北印度所进行的大起义的结果),而这正构成了《塞康德拉巴德之所见》所蕴涵的富有挑衅性的核心主题。这幅图像凝固了印度动荡的殖民地历史中的一刻,表面上看是对事实的忠实再现。而《塞康德拉巴德之所见》用一系列诗意的和论辩的姿态切入这一固有的印象──当被记录的图像从档案移入剧场时,这些姿态也同时置换着图像的权力。最终,这一作品要求观众具有进行若干形式的空间和时间旅行的欲望,而表演者、Raqs和乔达里则是他们值得信赖的向导。
脚本
塞康德拉巴德之所见
2012年5月17日
被隔绝起来的理性等于强权之声乘以其回声,减去民众之声的纷呈频率,再加上偶发变量。审视那强权之声与渐渐积聚的民众之声的频率之差,便可知晓民众的骚动产生怎样的净效应。
而偶发变量可被用来指涉任何情况,它可以是常年愤愤不平的民众所爆发的不期而至的狂喜,也可以是强者时而显出的疲乏;它甚至同样也可以是权力机器的耗损、维护和意外失灵;这些都将有可能改变这个等式,所以这个等式势必是脆弱的。
一粒尘埃在落定之前,是一颗炽热的微粒,在光中翩然起舞。
世界之主 帝国 行尸走肉 霸道 紧张 累计 战场 好好先生 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紧张症 老兵 末日之战 成本 会计 地窖 钻头 版权 二进制 系统 劝诫者 脓疮 无形 法令 银 牺牲 坟墓 召唤者 彩色影像 绞架 闪耀 炮艇 严峻 实业家 微积分 残骸 税吏 空降兵 说客 肿胀 搅局者 配置器 宣誓书 会聚 活着 粉碎机 知识分子 监禁 首领 补偿 评估人 飞艇驾驶员 种子 投机者 承运人 不屈不挠 锋利 药物 圆滑 水泥 支票簿 汽车 要塞 高速路 炫耀 买方 限制者 强有力 插曲 入侵者 压路机 金库 喷嘴 死路 长官 敏感指数 协约 证书持有人 取代者 电脑 毫不费力 混沌 弹头 例外 难以置信
多情的诗人们说,爱意味着失去。醉心市场的玩家们将某些失利视为东山再起的契机。因此,胜与败,并非泾渭分明,得与失,亦难以说清。
解鞍之马结束了征途。
三张图片:一头驴子正穿过一条空荡荡的路;一个男人站在一条空寂的大道上,一台测绘仪器遮住了他的脸;一个三脚架支撑着一台照相机,立于沙漠中的一座沙丘上,还有一片影子,显然是那缺席的摄影师,匆忙间将它留在了画面之中。
想这一路飞沙走石。眼见遍野征战遗骸,马再也不愿挪动半步。
许多地图,依旧是许多地图,各式各样的绘图法。现代航海图基于经度和纬度,通过某一运动物体与一个假想的静止表面之间的动态关联塑造自身。
纵观人类历史,在世上最庞大的水域之中的航行曾需运用一种不同的测算系统。该系统基于这样一种喻设——静止不动的航行者正处于交汇之处,一个世界迎面而来,另一个世界渐自远去。
不是航海者驶向岛屿,而是岛屿朝他而来,又从他身旁经过。
倘若我们能将时间折叠,就像折一张纸,将会如何?倘若我们能将时间折成一艘船或一架飞机,我们将经历怎样的旅程?
马亨德拉·拉尔·威尔玛 致 拉里·卡里瓦蒂,印度教女校,勒克瑙
1916年4月17日,40号战地邮局,法国
随信附上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一位英国女孩的死亡。你会注意到照片中有一个男人,女孩毫无知觉地躺在他面前的地上。她曾在比利时做护士,护理过伤员。
女孩被指控帮英国士兵经荷兰逃回英国,因而被判处死刑。她已不省人事,士兵们拒绝朝她的身体开枪。于是军官用左轮手枪崩开了她的脑袋。
米尔·山姆萨德·阿里 致 赛伊德·卡拉麦特·阿里·萨希布,德里
1916年5月
密拉特骑兵旅,法国
寄给你的照片拍摄于1916年4月。将它与去年4月拍摄的照片相比。你自己判断我写的是真是假。
古拉姆·拉苏尔·汗 致 他的父亲穆罕默德·纳瓦兹·汗,奥兰加巴德
1916年5月24日,塞康德拉巴德骑兵旅,法国
你说这张照片毫无用处,对我而言它却抵得上我的所有财富。
我在梦中也无法见到你,因此,能注视照片中的你,我深感安慰。
贾拉乌丁·艾哈迈德 致 哈吉·萨阿达特·米尔·汗
埃特马德普尔,北方邦,印度
1915年10月14日
鲁昂,法国
今天,我匆匆买了些图片,正将它们寄给巴希尔。我找不到更多张那个女人的照片了,她身披铠甲,目光如炬,直视苍天,俨然一位标致、俊秀的美人。我在寻找她的图片。已在多家店中搜求。四百年前,这位女子曾在抗击英军的战争中屡建赫赫战功。然而,她最终落入英军之手,被活活烧死。我想,这正是她的图片停售的原因。
亚莱特·汗 致 莫哈坎·乌丁
恰夸尔,杰赫勒姆县,旁遮普
1916年4月26日,锡亚尔科特骑兵旅,法国
我们被禁止写战争的详情。此外,一个人能写下什么呢?
倘若战争只限于一个区域,一个人或许可以描述它的细节,而这场战争已蔓延到整个世界,无一处能幸免。
萨依布·汗 致 他的兄弟阿卜杜拉·汗
112骑兵旅,沙达拉,斯瓦特,西北边境省,
1915年3月15日
电报公司密拉特分部,法国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当我回到印度,我会向你重述这整个故事,自始至终,就像《一千零一夜》。
照片像是拍摄于白日的晴光之中,或许是正午。一眼望去,它透出一丝忧郁感伤,一种对于逝去时光的壮阔乡愁,或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共鸣,来自那被捕捉到的瞬间:一处巴洛克风格的废墟,男人们摆着姿态,一匹骏马。
清晰便是可读。清晰能使我们深入诸般细节——姓名,地点,缘起,时间,进入,退出,或许,还有目的。
对清晰的执着又产生它自己的阴影。
露骨的谎言与赤裸的真相之间,是一片模糊地带。
我们阅读彼此,寻求迹象,并非因为我们晦暗不明,或必须渴求暧昧,而是因为我们的欲望、恐惧和经验仍然呼唤着一种能赋予生机的传达。
而后,我们的眼睛开始工作,游历。真相不再被阴影遮蔽,我们看到,“此情此景”不过是精心布置的结果。那些尸骨被清理,精挑细选,在幽暗大地的映衬之下,惨惨发白,如在一处栩栩画境。
倘若这是1857年印度大起义中起义者的身体,它们的骨架不会被保存得如此完好。
也许,非常有可能,它们根本就不是那些在锡坎德拉花园中被屠杀的起义者的尸骨,而只是一些道具,恐怖的人造肢体,“他人的尸骨”,被摆放在其中来营造场景,因为原来的尸骨已然“消失”,或者只是不够用来拍摄一张好看的照片。
原来的尸骨已然“消失”,或者只是不够用来拍摄一张好看的照片。
21世纪投下一个早产儿,来自未来,战栗降生。
在降临与短暂的隔离期后,白日的表象被探究,寻求生命物质的有机踪迹。来自第一批样本的初步报告持续显示出一贯的反常。
重要的问题仍然半死不活地悬置着:“是什么构成了生命的迹象?”。新陈代谢,生长,感知以及繁殖,以种种难解的方式进行着自我表达,或许,那些用于验证它们的指标也对此束手无策。我们如何知道,在那些我们至今尚未知晓、或无法想象的生命形式之中,新陈代谢、知觉或是繁殖是如何进行的?我们怎样才能知道?
宇航员同志,当你遨游太空,你如何辨识生命的迹象?
时空是否会扭曲你的感官?
别了,宇航员,一路平安。
骨头。
如果这两百零六具成年尸骨可以各自发声,他们都将高唱身体的颂歌。藏骨堂将成为歌剧院。胸骨彰显其主人的骄傲;肋骨好似忧伤的歌队,为那振翅的心扉低唱挽歌;腓骨,胫骨,股骨,击鼓以和,浩浩颂歌,气势磅礴;跗骨与跖骨,腕骨与掌骨,桡骨与尺骨,歌唱平衡与灵巧;尾骨由底层击出一个怨诽的音符;额骨在头盖骨上忧心忡忡。
这些骨头功能各异,类别不同,它们低语,嘶鸣,各讲方言,抑扬顿挫,欢笑,哀哭,唱着曲调,或者走调,完全乱套。唯有那寂寞的舌骨,含糊的舌骨,可能会以讥诮的沉默面对这众骨喧哗。舌骨会管好舌头,它知道每个生命,都只配得如此这般的喧哗或沉默,亦如所有其他的生命。
当骨头们停止歌唱,哨音与幽怨的赋格也暗灭了声息,照片的沉默,定格瞬间的沉默,又重新开始自我述说。
(翻译:戴章伦,校对:陈韵、施瀚涛)
Interior of the Secundra Bagh after the Slaughter of 2,000 Rebels by the 93rd Highlanders and 4th Punjab Regiment. First Attack of Sir Colin Campbell in November 1857, Lucknow. Albumen silver print, by Felice Beato, 1858.
塞康德拉巴德的内部,在2000名起义者被第93高地兵团和第4旁遮普军团镇压屠杀之后的场景。科林·坎贝尔爵士的第一次进攻,1857年11月,勒克瑙。蛋白银版照片,费利斯·比特,18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