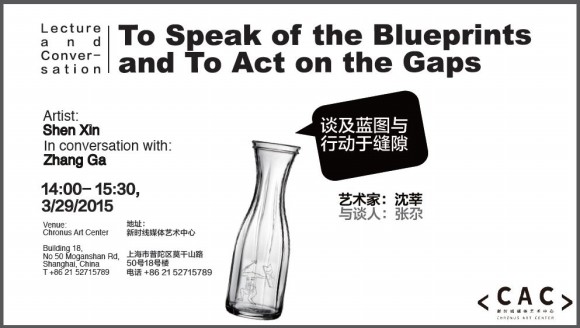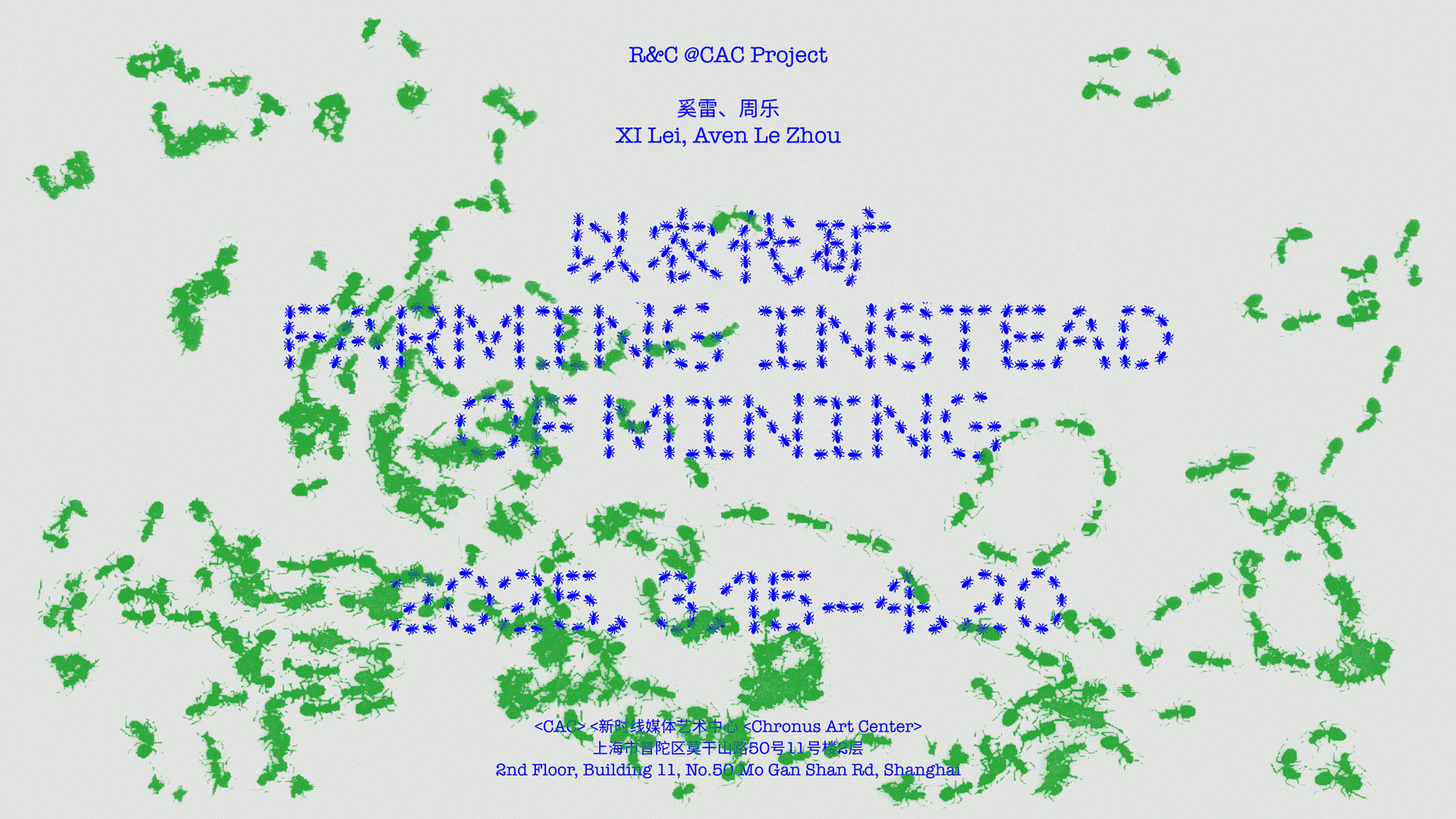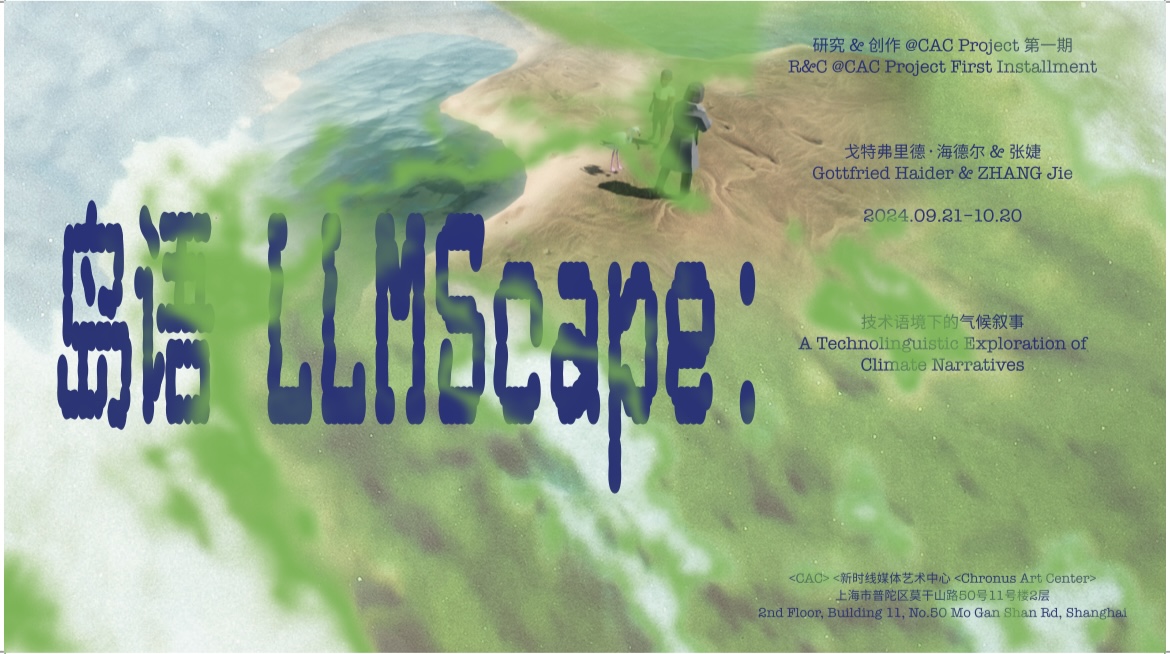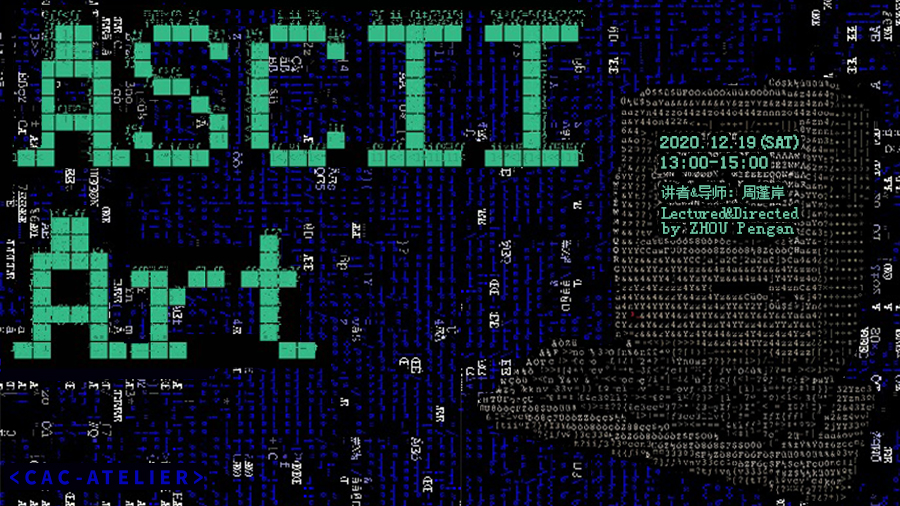嘉宾:沈莘、张尕
时间:2015-03-29 14:00 ~ 2015-03-29 15:30
地点: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上海市普陀区莫干山路50号18号楼)
语言:中文
本活动免费,请通过邮件预约 membership@chronusartcenter.org(注明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预约人数)
活动简介:
3月29日,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将为您呈现2015年“CAC中国艺术家学术奖金”获得者沈莘的艺术家讲座以及她与媒体艺术教授、策展人张尕之间的对谈。活动将围绕沈莘即将在伯明翰艺术与设计学院(BIAD)与中国视觉艺术中心(CCVA)进行的研究项目展开。
沈莘的研究聚焦于她对非物质性劳动的兴趣,以及此类劳动在研讨会、会议等情景之下与动画和数码生产之间的关系。获奖项目名为“平展的形而上学”,计划组织并邀请一些来自理论、艺术、政治等领域的实践者来参与。沈莘关注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讨论环境中的位置,试图在言说与行动、思考与交锋、批评与吸收的缝隙中绘制她的蓝图。而此次活动,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皆可视作是对沈莘这一项目的一次预演,呈现了项目中的一些工作方法和核心概念。此外,沈莘还将介绍自己之前相关的创作实践:从动态影像开始,还包括了虚拟现实与人物、公共提案、沟通界面、自出版和旅游景点。
讲者简介:
沈莘,生于1990年,2014年获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美术学院艺术硕士,现生活工作于英国与中国。沈莘曾被“彭博新当代”选中在利物浦的世界博物馆、伦敦的ICA和康沃尔的Newlyn艺术画廊展出作品。沈莘也曾为ICA策划“艺术家电影俱乐部”项目“非正统主人 (Unorthodox Hosts)”,并曾被Kirsty Ogg选入MA Star for Axis Web。她曾参与过的群展包括:第十八届日本媒体艺术节(东京);“并不等同"(W139,阿姆斯特丹);“彭博新当代”(世界博物馆,利物浦双年展,ICA);“21世纪放映”(Chisenhale画廊,伦敦);中国视觉节(国王学院,伦敦)。
张尕,媒体艺术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馆2008、2011、2014 年国际媒体艺术三年展艺术总监/策展人,列奥纳多丛书编委(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CAC中国艺术家奖学金”简介
“CAC中国艺术家奖学金”由新时线艺术中心(CAC)与伯明翰城市大学下设伯明翰艺术学院(BIAD)共同创立,旨在为正处于艺术生涯关键阶段的年轻中国艺术家提供一个振奋人心的机会,以助其进一步发展他/她的艺术事业。
奖金获得者将会有长达半年的时间完全深入到BIAD学习、交流、创作和研究,并成为伯明翰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学院研究部,特别是中国视觉艺术中心(CCVA)的成员。在项目最后,奖学金获得者将在伯明翰艺术与设计学院(BIAD)举办一场成果展。
讲座回顾
——————————————————
讲题:《谈及蓝图与行动于缝隙》
日期:2015/03/29
艺术家:沈莘
与谈人:张尕
第一部分 沈莘:谈及蓝图/行动于缝隙
[讲座概要]
项目的大致构想是邀请理论家和学者在研讨会现场用自己的脸(或表情)和身体激活《山海经》里的一些人物和角色,同时通过屏幕来开展讲座、与观众互动。
我将谈及拓扑(topology)的概念,作为介入我的项目的一些点。拓扑学展开来讲是关于如何定夺地方、点、空间属性、布局以及对内部的定义。明显的联系是做3D模型时所必须掌握的网状拓扑结构,还有《山海经》作为古老的地理学和社会文化拓扑的知识记载。随着认识的发展,以及各种科技将其视觉生触到各个角落,《山海经》的版图不断扩大,认识论高强度的依赖着相对论。节点之间互相传达数据和对累赘节点的包容,使我们能用拓扑制作各种次元的再生“数字他者”。
所谓跨领域实践,在如今艺术工作日益职业化 (我所指的职业化包括.org, 团队,公司,和个人机制等等现象)的环境中,工作语言积极地介入各领域,如科技、生态、城市建设、哲学、理论等,实践者也在运用着拓扑学的方法和理论基础。
我试图使用拓扑学来探讨话语权,通过它将一种经验通过翻译而不代表的形式呈现出来。它对所谓累赘节点的包容表达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并且是可以由缝隙中衍生长成,独立于各领域被定义的内部之外的结构。对我而言,它的意义在于探讨美学的功能性。
如我之前提到的职业化,我们不再只是去工作和创造,同时我们也都像演员般在演出,并邀请同事和其他人等来观看。这也不局限于艺术领域,也适用于理论。它好比多个摇滚之夜的排列般,国际的与本地的,生产出一张又一张的顺序表和不同的组合。我们在资本和科技的更新与革命中,看到了非物质化劳动与创造性劳动力的重要性与被需要性,也同时在消耗着自己。而劳动力的非物质化也同样延伸至劳动成果和价值的非物质化。
伊斯特·莱斯利(Esther Leslie)在她的著作Hollywood Flatland的书写中衍生出米老鼠和1930s德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以及米老鼠作为蔑视资产阶级的象征图形,更是可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抗争的大众和流行文化之星。试想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和米老鼠握手的场景要动起来是需要多少桢不同的图组成,而从30年代起华特·迪士尼在全球资本化环境下的壮大,脱离了与资产阶级抗衡的角色,3D动画则更是用建造骨架数据的方式取代了一张又一张的动画涂抹制作过程。数据的拓扑衍生出了储存的空间,并且通过这个空间对于劳动力和价值重新定义着, 也对认识我们自身的身体产生着影响。劳动力日益非物质化,而剥削行为也变得日益难以分辨。分辨与判断也被剥夺着批评性和可塑性。因为对于任何机制与结构的批判都似乎可以通过流动的资本而被消化,成为罪孽的赦免牌和美学借口。
对我而言有挑战性的是当科技更进一步地结合人体感官并欲带领其进入新的机制与转换时,我们的感官成了机器运作的一部分, 使用科技者也有可能成为科技的一部分。这些技术在创造时就已经考虑了我们的身体的存在,将我们的身体编织入它的程序中。并且大量的运用欲望与经济的联系,比如oculus rift浸入色情业,或帮助远距离情侣解决生理问题。
通过与科技为谋来发声,同时在过程中也能与之抗衡,在距离感和亲密感之间塑造每一个动画人物和知识传达的途径,这也是我会交给受邀前来参加讲座的理论家的课题。与我很多其他作品一样,这个项目也有意识地塑造起一个类似于战场和搏击的环境,虽平静但需要观者在里面有所挣扎。
如今的数字化和科技让我们更加得心应手地自我开采和利用自己的劳动力。我的项目提出的另一议题便是去争夺并探讨自我利用与被利用的方式,以及我们的局限性与边界。拓扑学给予话语权新的解释与可能性,我们得以去组织,而不仅仅去是单一的去创造,也同时得以审视我们的判断力。在不同社会环境下艺术工作者都经历了在判断力上拓扑的现代主义,在历史也被赋予主观流动性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再通过客观的主体去形成我们的判断。这个项目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邀请的参加者都将探讨为美学所用的美学、美学和知识的内部构造,从而展开赋予美学他者权利的蓝图。
《教育戏剧 —— 一个原型》(Lehrstück – A Prototype)直接面对oculus rift这样的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可能性与新鲜感开拓出一个不去质疑的绝对空间,也保持一种批评与被批评的开放空间。这对我作为组织这个项目的人来说也是适用的。它涉及到在全球化下发展的旅游经济,以及带有迷恋性的去物化他者如其他民族、地域、自然景观等行为。通过摆明的事实和现象并运用新的被大众化和在大众消费范围内的技术来试探使用者对于道德和政治正确的优越感。同时这个项目也讨论着在现代主义进程中留下的纪实影像的遗产和对它的质疑,比如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的《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无数次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利用与被再创造,最终照片成为具有颠覆性的宣传工具。美学受到来自于准他者设置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优越感的压抑,并在这样的标准下被观看着,方便了资本的流动。但在我看来这抑制了美学的权利。可是宣称无道德标准而对此类主题完全不去思考且有意避之的艺术实践者同样也是在处于优越的位置在发声。因此,我关注的是如何在美学中拓展一个内部构造,不受制也不以抽象为流动资本。
在这个虚拟空间里的主体和拼贴状的男人、女人、小孩和牦牛都来自于我父亲在四川的藏区以及西藏近20年来拍的照片。这个项目也同时和我的一个影像作品《细数祝福》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展览时处于相对的位置。这部影片也是在探讨道德、美学、图像经济、教育与实践者之间的互相受制与价值转换。在制作这部影片的最后阶段我开始有了开拓消极空间中的消极空间的想法,也就是开始对绝对消极的天真和烂漫产生了新的理解。
以我最近的影片《付出式批评》(The Gay Critic),提出了一个新的批评家的位置,不以批评和被接受为模式,而是以建立关系为模式来“批评”——围绕着酷儿美学、全息图片歌手、临时工如酷儿般的亲密互动与三岛的身份象征展开。在我的理解中三岛的身份介入了美学能够重新去理解反应的(reactionary)的空间,也建立了美学能够真正脱离政治但也不卖身于抽象经济的可能性,也就是美学的必要性。奥利弗(Oliver)唱着三岛所描述的有关在战争中能够被摧毁和对于死亡的幻想。一个虚拟的声音数据向往着死亡和毁灭的意义,是否是主体与物体之间不去区分的最后结果?这是我组织的讲座也许可能包含的主题之一,即“死亡的科技意识”(the technical consciousness of death)。对于死亡的想象也许是我对思辨的实证主义(speculative realism)的一种理论认识的延伸和它作为必然而又未知的主体经验的载体的理解。来自于对影像作品作为从a-b这样推移的时间形式的固执性的欣赏和对这样的固定点运动的时间的可能性的认可。时间的生死和图像的意义之间的联系可以这样理解:一张图片的出现预示着另一张图片的“死亡”,一种颜色的在图标上的消逝与其他的色彩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最后我想提出,组织这样的实践方式本身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所说的探讨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public)是一个具有导向性的词,它是以方法论做为基础的认识方式,更多描述一种方式,而并非主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 也不是去催促知识分子或艺术者扛起已知的社会责任。它是一个定义的过程。
第二部分 沈莘x张尕对话录
[对谈全文+观众提问]
//翻译而不代表//
张:你提到的“翻译而不代表”(translation without interpretation)这个概念如何理解?
沈:去翻译这个经验,但是不去代表它。
张:德勒兹(Gilles Deleuze)强调:翻译就是去代表。因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转成另外一种语言,是一个解读的过程,一个指向的过程。“翻译”与“代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悖论,但这两件事都是必须要做的。如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言:“巴西利亚的内部就是巴西利亚”(the interior of Brasilia is Brasilia),它不是代表别的东西。 又比如,我在描述这个瓶子的时候并非描述瓶子本身,它是一个能指(signifier)。这当中涉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代表”(representation)与“被代表”(represented)之间的关系。这是当代艺术中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目的和行为动机。在你的研究计划中,试图以《山海经》中的动画形象来呈现受邀前来参加讲座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山海经》中的头像代表的是谁?当你赋予讲者一个头像的时候,你给了它一个意指(signified)的可能,而同时你又要做到“翻译而不代表”。你如何化解这样的矛盾?
沈:首先,“翻译而不代表”是具体要在拓扑学中讨论的。对于一种经验,比如发生在这个舞台上的经验,可以通过发生在舞台下面的经验来理解它。换句话时候,在讲座现场,讲者的感受可以通过观众的感受来理解,反之亦然。我所说的“翻译而不代表”指的就是不去看这个事件所在的位置,而是通过看另外一个处境来看这个事件。一个直接的例子是皮耶尔·修贺(Pierre Huyghe)的作品A Journey that Wasn’t,当中在公园里有一个管弦乐团在表演,同时又用南极圈去探险的这样一种形式、一种不同的环境去描述这样一种经验。“翻译”并非是要用来解释或代表,而很可能本来就是对“代表”这个东西的一种质疑。
张:你在赋予讲者一个《山海经》里的头像,赋予《山海经》里的角色一种人格的时候,其实给人创造了一种联想的余地。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内涵上,《山海经》中的角色好像一种能指,对应一种人格。
沈:《山海经》中的人物不那么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它可能是描述一种性格。比如夸父,它有一种性格,但它并没有一种十分具体的形象,不能完全将它物化。况且,我们现在看《山海经》或确定地理位置的时候,始终是从一个主体的认识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山海经》本身具有一种流动性。它的不确定性和它在认识论上的摇摆不定的性质决定了如果你给予它一种这样的图像时,它并不能直接去代表,而仅仅可能在图像上是一种代表的关系。
[批判的必要性]
张:我讲的“代表”并非比喻意义(figurative)上的代表。它与你提到的其它几个概念,如“批判性”(criticality)、“消极空间”(negative space)一样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代表”和“批判性”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你要批判某样东西的时候,先要假设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而这个对象本身需要一种形态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运用一定的代表的(representational)方法或策略。因为艺术不是一种直接的政治行为,它必须通过一种转借的手段来达到它的批判目的。再现这种形成的操作模式、生产系统,以及当代艺术的整体的批判就在这样的逻辑里运行。你提到批判性的质疑和对消极空间的偏爱,可否在这方面谈一谈?
沈:当一个人在面对一则批评或一个展览的作品的批评时,与这个批评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服从性的关系。我们习惯以一种服从性的关系来看一种批判(如批判性的文章、展评),试图去理解它的意思,得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立场。我觉得这种方式并不是那么具有活力或生产力。相反,如果一个批评家在批评一个展览或一个作家在写作时是通过建立很多关系,那么涉及的范围就变大了,批判的东西就变多了。在想法上建立与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同时来形成批评的机制,这同“代表”也有相似之处。
张:你讲的是批判性的方法的问题。我想讲的是批判性作为当代艺术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criticality)。你提到资本主义或资本本身(社会资本)有一种对批判的内在的需求,自残是它的自我保护的必要代价(the necessity of self-muitilation, Alain Badiou)。今天整个社会的资本运作及其模式都需要通过“批判的他者”(critical other)来维持它自己的生产机制,一种自我生成、自我保护的机制,所以批判是它的需要。而当艺术家举起批判的大旗时,是在迎合一种资本需求。这样一来,我们要如何看待批判性?例如,你提到的reactionary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叫“反动”,是个含贬义的概念,但在英文中并无所谓褒义或贬义。它仅仅是相对行动(action)而来的反应。你可否在这方面多作一点阐述?
沈:关于批判的必要性,在我之前的创作中有一个方法是给邪恶的东西或者说所谓的不道德的东西一个空间。我在伦敦读书时和老师交流,他们认为像在旅行中拍摄少数民族的照片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道德的,它是一种对少数民族的客体化(objectification)。
张:你是作为一个它者(other)。
沈:对。我认为将这样的事情硬性规定为不道德,这样的形式本身是一种政治的语言,并不是美学的语言。它是用“去做”与“不去做”来区分,并不是用美学能够做到的一个权利。在我的影片《细数幸福》中我试图用我与我父亲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为什么他拍摄很多少数民族的照片、他这样做的原因和最后想要达到的一个结果,以及之间的一种循环、在经济上起的一种效应。这是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给所谓的不道德的行为一个空间,在只有美学能够做到的事情上给它一个空间,去理解它。
//美学的权利//
张:在西方的语境里,“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尤其在艺术文化圈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你刚刚提到的对少数民族的客体化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方式,是从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主流社会对文化生产者或艺术家的一种道德需求,也以此作为一种道德制高点来建立起它自己的权威。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的西方知识分子、学界激起了很多反动和质疑。你所讲到的思辨的实证主义(speculative realism)的这一批年轻的哲学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质疑这样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因为它桎梏了思考的可能,也把思考建立在某种前提上。事实上,思考并不需要建立在某种前提上。
作为一种回应,你讲到用审美的内部结构来重新构建,可以用平白的语言来阐述一下吗? 当然你的艺术创作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在作回应。你如何看待自己不同于当代艺术的一种审美或美学情绪?你认为你的美学是一种政治学的延伸,抑或政治本身是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是在构造形态还是在语言这样一种过程里面自然产生?
沈:我想做的事情是赋予美学一种权利,但这种权利不同于政治权利。它并非一种去受制或是去区分阶级、经济上的区别,或是给予利益的一种权利。它是没有利益的一种权利,是去思考,是不应该有前提的。然而,与此同时也不可能忽略社会、政治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只是这种权利的机制本身存在于语言中,无法绕过它,只能通过探讨美学中本来就有的权利去尝试去做这件事。我可能不太同意所谓主流美学或其它的实践方式中的一点,是作品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代表”的关系,艺术家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做一个作品就是要表达这个事儿。这种做法本身应该被质疑,这是应该被摒弃的一种关系。
//科技的它者//
张:这种艺术现象从8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艺术界,自后结构主义的引进主导了整个学界和艺术界的道德依据和行为方法。我昨天在王功新的展览里看到那一代人有那一种情怀。他们桎梏在这样一种政治、社会文化的必然性里而无法考虑人之外的作为艺术生产的对象。你属于90以后的这一代人,可能没有这样的负担。你提到科技与人体的距离,使用“科技的它者”(technical other) 等这些表述,好像已经在摆脱一种以人作为唯一的艺术生产对象、生产主体的逻辑,是否有可能在思考人之外作为主体的可能性?
沈:应该是朝着这样一个方面在发展。但之前提到的代表机制本身的性质,跟离开中国有关系。作为一个离散华人(diaspora)在国外的经历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如什么东西能够代表我。于是发觉语言所及的“代表”不过是一个假设,自然而然形成了不要理所当然地使用“我们”这样的词汇的意识。我们所讲的话虽然是从个体的嘴里说出来,它其实含有集体的概念。因为语言的组成本来是一个集体的功劳,语言中的这个集体概念和代表机制几乎无法摆脱。所谓的集体和个体之间的概念,也是我所关注的一个东西。
至于“科技的他者”这个概念,我联想到新陈代谢,即怎样使用技术的方式使得我们的新陈代谢的方式有所改变,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比如,我的作品《付出式批评》中奥利弗(Oliver)这个虚拟声音数据,它歌唱的时候对我们听觉的触动,以及他歌唱的内容,一些关于暴君、暴力、死亡与毁灭等的幻想对我们听觉的触动。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而要想象它在歌唱这样的内容,就是在听觉上和思想上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包容这样一个技术上的东西。
//个体化与身份的代表//
张:还有一个问题,你谈到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吉尔贝·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讲到一个“个体化”(individuation)的概念。他是很重要的一个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很多灵感(如 the plane of immanence的概念)都来源于他。“个体化”这个词指的是一个过程,个体不是一个既成的概念,不是一个理所当然(taken for granted)的概念。我们在讨论哲学或美学的时候,它假定的前提是本体论的,亦即已经假想一个本体作为讨论的基础。可是西蒙栋的“个体化”提出了一个过程,它跟力学里的亚稳定状态(metastability)这个重要概念类似。亚稳定状态是一个不断沸腾、转换的过程,它可能转换成固态、液态,而当它转化成固态时亚稳定状态就消失了,也就是从“个体化中”(individuating)变成“既成个体”(individuated)。这个过程还可以再转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还讲到becoming的概念,就是一直在becoming之中。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代表”(representation)的概念是首先假设你是一个什么身份,然后再想如何代表这个概念。然而,我们的身份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永远处在一种个体化的过程之中,生命就是一种个体化的过程。西蒙栋的这个individuating或pre-individuated的概念对于我们去质疑或化解“代表”这个强大的概念是十分效的方法。
沈:我读到您在《齐物等观》的展览中论及becoming这个概念。德勒兹还提到situ这个概念,它是在原点,但在不停变动。在我看来,它与道家思想中的物化的观念也是有共鸣的。我刚才在论述拓扑学的时候提到一个所谓的节点,如在做一个3D模型时有很多的点,有些点是完全没有用的,可这些点不能被摒弃,因为在技术、编程里已经包含了这种语言,如果摒弃,这个程序就无法成立。又如男女性别的问题,我们在承认男女性别的存在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其它性别身份的人的存在,这是中间的一种转换,也可理解为所谓的节点。
//技术与艺术//
张:最后一个问题。你提到技术,也运用很多技术作为你的创作方法以及你的作品本身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你怎样看待技术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技术是一种形式状态,还是一种媒介?时下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艺术最重要的是概念,观念先行,无论何种形式都不过媒介而已。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沈:我觉得在使用任何一种技术时必须思考技术本身所存在的意义。例如,为何它会编织成像虚拟声音库这样的东西。你去运用它时就必须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当你在程序中输入一个字如critic时,这个单词就变成kh r I t I k 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为什么要用类似于象声字的程序之类的东西做电影?它与我的电影之间的所谓美学和语言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我必须去考虑的东西。我需要考虑这个程序是怎么形成的,而不能假设我有一个概念,用这个东西做出来的声音比较符合。拿3D 运动捕捉来说,它的形成过程需要哪一些数据,我需要去训练它,训练那个卡通形象,使它认识我的脸,它才能依照我的脸做动作。而训练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是你服从于它的过程。这些都是我必须考虑的东西,它们不只是一个形式或一种空壳。
//观众提问//
问: 你刚刚提到一个批评中的“服从”的概念,当读者面对一个展评的时候,是批评家对既有关系的运用导致了这样一种服从,同样在艺术家与其的作品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就你的创作而言,你希望观众在面对你的作品的时候,也是一种服从的关系吗?
沈:一定不是的。我所做的是一个类似于搏击的环境,没有那么剧烈,但是我做的东西一定要让观众在观看时产生一种急迫感,能够自己找位置,自己去定位和思考的一种运动。我希望我做出来的作品和观众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我不会给观众设定好一个位置。我的创作是一个想法的过程的体现,并非表现一个既定的东西,因为我对代表的机制本来就是完全反对的。另外,我做出来的作品本身就是有机的,它的思想方式编织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有机的东西。当观众在观看时,它是一个被曝光的状态,但它一定与“服从”无关。
问:在批评的世界里,你觉得观众和批评之间会形成这样的搏击的状态吗?
沈:在我现在读的书里,小说有这样的形式。比如说一个伊朗的策展人叫Tirdad Zolghadr他写的一本书叫《软核心》(Softcore)。 他写的是关于艺术家和艺术世界的事情,比如说他写一个策展人在一个餐桌上突然开心地笑起来,然后鼻涕就流出来了。这是在丑化艺术界里的一些大咖之间的一些事情,非常具有挑动性(provocative)。我觉得只要去做,写作和语言是很容易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的。
问:关于艺术作品的定义,你提到你不喜欢的一类作品,在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是一个表达的关系。希望你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你的这个说法的立场。
沈:就是把立场这个东西也看成是一个流动性的东西。我所说的艺术家跟自己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表达的关系,是说作品不是艺术家想要表达东西的唯一的呈现方式。比如说你读一本书或者读一篇文章,你可以从中吸取一些东西,但你同时可以看到写作者的一种性格取向,那这就是一个认识的方式,但是一个写得好的作家并不是完全想要传达他的意思给你,让你只有接收这样一种方式。而是你可以投入他的一个思考过程,然后运用他所想的东西来思考你自己的东西。让艺术作品成为一个工具,这是我提倡的一个做法。
问: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你考虑到这么多层面的东西,但最后在你完成的作品的状态中,观众到底能感受到多少?这当中你要解决技术性的东西,可能最后会生成你自己的工作方式,生成带有技术感的东西。
沈:观众能够感受到的不是我能控制的东西,也不是我想去控制的东西。我只能说,我想给予用美学去思考这样一个形式最大的价值,给这个思考的过程最大的价值。
张:我补充一点。我觉得正是在这种过程里你形成自己的所谓形式、风格。常常有一些艺术家在跟技术打交道的时候马上把技术这个东西隔离开来,认为艺术是艺术,技术是技术,好像技术跟艺术完全是一个附庸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会牵涉到很多表演、行为艺术,也有很多技术含量的东西,而很多人对这些技术完全不了解。你是在这个过程里慢慢找到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必须跟你的作品的内容形成一种必然的有机的关系。这个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只有这样的形式才有这样的内同,只有这样的内容才有这样的形式。或者说,只有这样的技术才有这样的艺术,只有这样的艺术才有这样的技术,是在这个过程里发展这样一种语言。
最后,还是回到美学的内在的关系和逻辑来表述这一重要意义,否则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艺术家可以是一个政治家、制作人、人类学家、科学家。这个观点看似从广义上扩展了艺术的界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艺术还是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有它内在的逻辑和它对语言的一个基本范畴。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艺术的问题是在一个大环境下的一些具体的形态而已,它与哲学思考的演进是一脉相承的。二十世纪的哲学,尤其是60年代以后,本体论渐渐退出舞台,认识论主导了哲学思考的整个领域。今天为什么主体论又开始回到了哲学讨论的中心?现在的思辨的实证主义(speculative realism)就是要重新把本体论引到哲学的最根本的一个原点中来考虑。今天讨论的艺术家可以是制作人、人类学家、神学家等,但就是没有说艺术家就是艺术家。这个时候艺术这个本体的概念又要回归我们讨论的焦点。
沈:我想最后提一下张尕老师写的文章。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你不会直接提及“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你会说“去思考”。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去形成一种所谓的语言的时候,也是去进行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而我把所谓美学和艺术家的位置放在一个“去思考”的位置,很多东西都可以变成思考的主体,所以每一次创作我都会去了解这个技术的含量——它为什么是这样,它和我所做的东西有什么样的连接。每一次都是新的思考方式。我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不去形成一个固定的语言系统,而是一个流动的语言系统。
张: 这又回到我刚才讲的individuating的概念,一直在becoming,在不断地生产、演进,不断个体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创作就是本身在不断地个体化的状态里面。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给定的(given)东西。